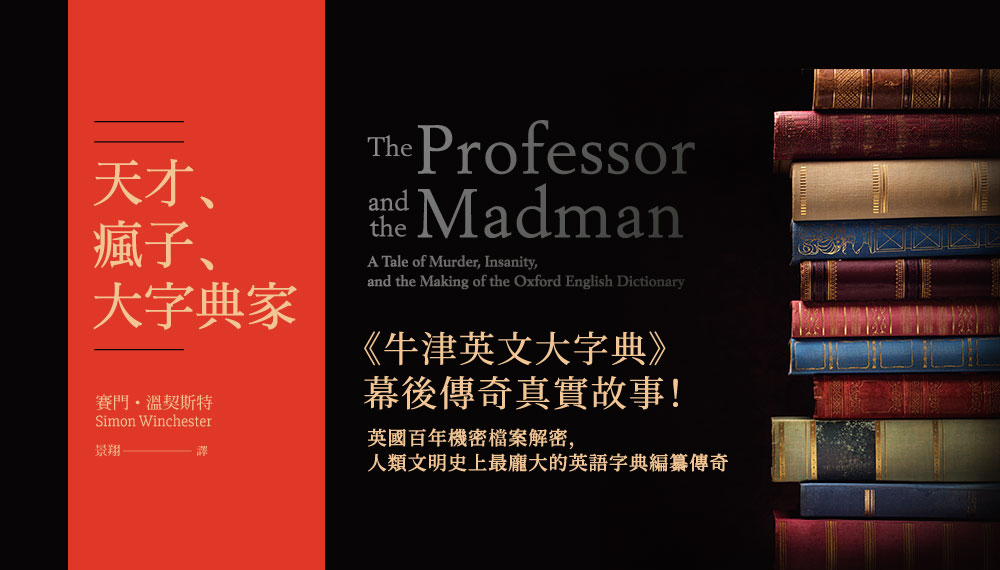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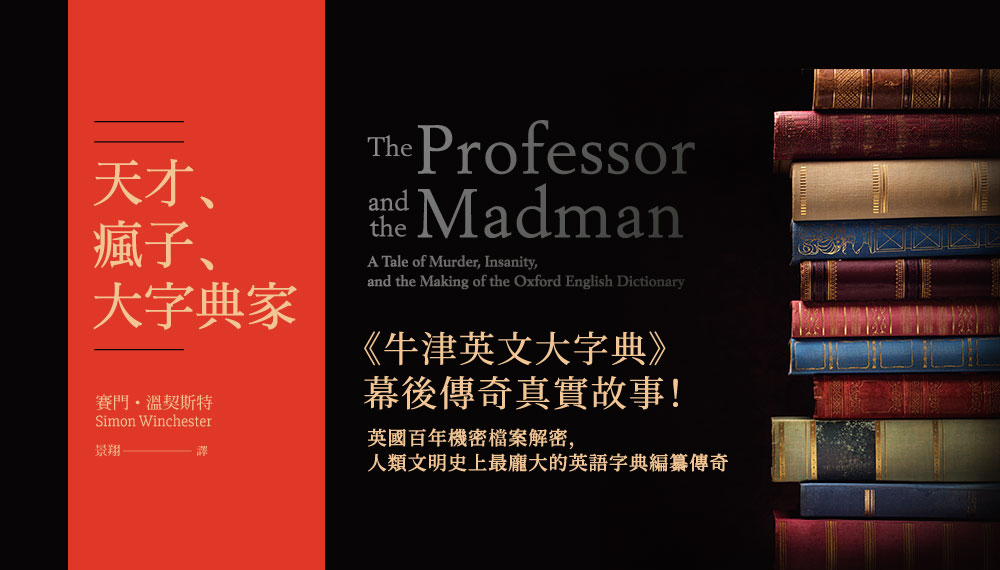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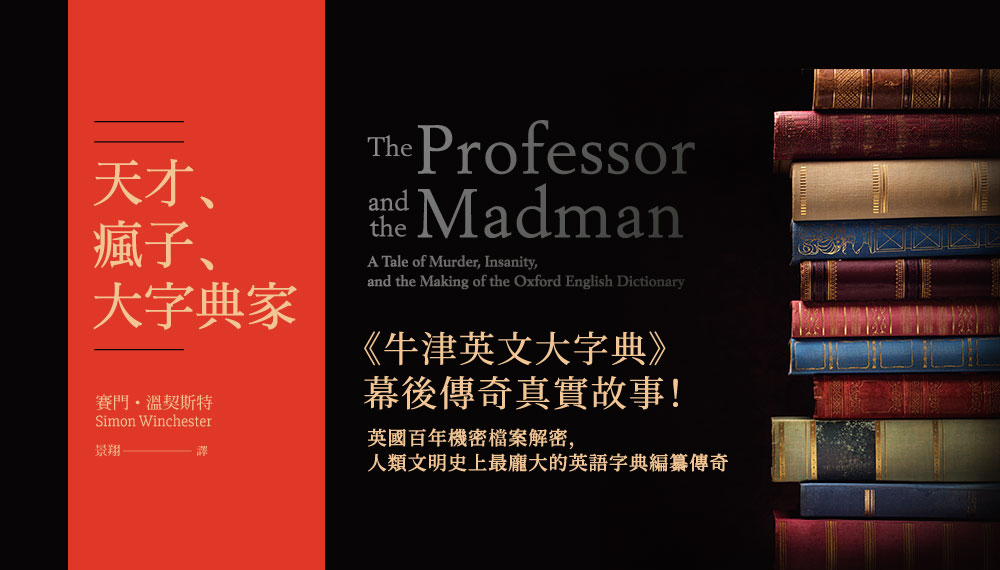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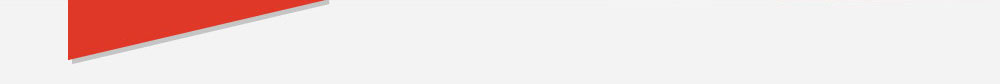
譯者序
譯完王爾德原著的《教我如何愛你》之後,總以為再沒有什麼書在迻譯過程中需要那樣不停地翻查《大英百科全書》和其他的參考書籍了,想不到這本《瘋子‧教授‧大字典》又讓我深切體會到「書到用時方恨少」這句老話,實在說得大有道理。
這本書的作者當然不如王爾德的腹笥那麼寬廣,但對文字語言之了解與喜歡賣弄,則有過之。初譯之時,我甚至覺得作者以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書寫方式寫作,恐怕只有使用文白夾雜的「新民叢報體」來翻譯才能傳神。可是一來個人的功力未逮,二來也怕造成一般讀者的不便,還是未敢輕易嘗試,只是有些地方配合原作的行文與遣詞風格,也學著掉了些書袋而已。
原作中常有玩弄文字趣味,將同樣的意思以不同的用字和講法重複敘述,中譯時也只有勉強對應譯出,可能因此有些句子會讓讀者覺得疊床架屋,那只能歸咎於譯者在表達上的「變化」不足。
談到語文問題,譯這本書時真正讓我和負責編輯的同仁考慮再四的是,究竟該把OED譯作《牛津英文大字典》,還是《牛津英文大辭典》。
從《辭源》或《辭海》上,都可以看到「字:文字也,形聲相益謂之字」的說法,而「字典」則都解釋為「即字書」或「字書之一」,而所謂「字書」就是「譯注各字之音義,及引證書籍,以備檢查者也」。
至於「辭」的解釋是:「言之成文者曰辭」。《辭源》一書中沒有「辭典」這個辭,而《辭海》中則刊錄了「辭典:蒐集各類學問中之單字片語及重要學說,逐一解釋,以備檢查者,曰辭典。」
從這些定義來看,「字典」和「辭典」分明是兩種不同的工具書,不過這種分別,大概只存在於中文,我們的方塊字,雖然也有單字成辭的,但更多的是以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組成辭,至於英文等拼音文字,以字母為基本單位,拼組成的單字,其實譯為中文時,幾乎都是辭。這樣說來,似乎應該把OED譯為《牛津英文大辭典》,但最後仍然決定譯為《牛津英文大字典》的原因是Dictionary這個英文單字一向譯為「字典」,而且書中談到的都是word,一般也都譯為「字」或「單字」(本書中有時因應需要或為行文變化,也有譯為「字辭」的),再加上OED的特色在引用很多的例句來為單字定義和加以解釋,以及對字源作考證,也都合於前面所引的「字書」的定義,想來譯為「大字典」應該是適切的。
因為這是一本談語文的書,其中不免有太多不常見到的字,也有很多目前不只是「罕用」,也早已「不用」的字,一般的英漢字典裡當然不會載有,手邊的《藍燈書屋英文大字典》和《韋氏大字典》這兩本英英大字典,也有查不到而無法確切了解其含意的字,只好以「原文」入書,以待方家教正。
而書中隨時會提到當時英國政經藝文等各界的名人,有些是現在仍然讓大多數人耳熟能詳的,但更多的是只有在某個專業領域裡的人才有機會再接觸到他們大名和相關事蹟的。為了讓讀者有個基本的了解,勢必要寫註清楚。但是如果滿篇括弧加譯註,雖然既可表示譯者的敬業與用功,又可增加稿費(想想每個名字下一對括弧加上譯註兩字和一個冒號,就是五個字,積少成多,實在十分可觀),讀者看來卻不免時受打擾,所以都將關鍵性的相關說明資料直接寫在人名之前,以使行文流暢。又或有極少數詞語,原作者寫來太過簡約(例如巴西的一種小魚Cadiru),則參考有關資料補充,以便讀者能充分了解。此等做法,以狹義的「忠於原作」來說,或不免有可議之處,是必須在此說明的。
書中人名的中譯,除約定俗成,行之已久的譯名外,大多參考東華書局所出的《英漢大辭典》,而有關精神病之各種專門名詞,得王浩威醫師指正;原作中提到的「掃羅」經聲樂家及名音樂節目主持人佐伊子賜告是韓德爾的清唱劇,都使本書的譯本更形完備,在此表示謝意,也讓從事譯作三十多年的我體會到:要把翻譯工作做好,自己的努力,興趣的廣泛,常識與知識的吸收,以及實際經驗的累積等固然重要,更重要的還是要結交各行各業學有專精的好朋友。